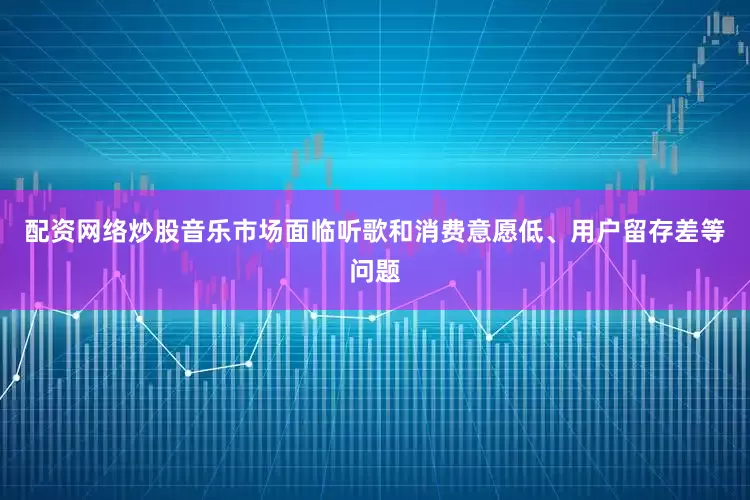《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南京是国民政府十年经营的首都,具有极重要的内政和外交意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南京政府蓄意把战火延烧到长江下游,却不曾把南京防卫部署列入整体作战计划之中。

考其缘由可能是对上海战争过于乐观,不相信南京会遭受波及。以致南京防卫战一直要等到上海局势恶化到无可挽救地步时才被提上日程,显得万分仓促。
1、仓促的南京保卫战
依据多项记载,南京政府迟至11月14日才首度召集高层军事会议,商讨保卫南京事务。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人。陈诚在事先已经极力主张不要防守南京,而且也获得蒋介石初步同意。
但是唐生智自请誓死守城,并且嘲笑华北将领傅作义个人历史污点,正是他曾经不能与城共存亡。就在会议当天,身为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还不断请求蒋介石,去询问张发奎能够维持淞沪前线几日?而在此几日之中,我方又可以做出何种准备?种种慌乱景象历历在目。
两天之后,中央政府开会决定守南京的办法,由唐生智出任长官,期望守三个月至一年。与此同时,汪精卫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也报告了政府机关从南京向外地疏散办法。在过了3天举行的会议上,虽然白崇禧主张中国今后应该进行游击战,但是唐生智认为南京不可以不守,蒋介石也同意。最后与会者认为委员长身为国家最高统帅不宜担任守城将军,而唐生智又主动请缨,因此在1937年11月20日政府宣布唐生智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
有趣的是,蒋介石早在南京防卫战筹备初期就已经认定南京不可守,但是出于感情因素,又不能弃城而去。
虽然此时他已经不再坚持“死守”,而只求多守些时日以便挽救物资,可是何应钦却指出,仅仅是军政部一个单位的重要文档设备就需要100列火车厢方能运走。因此政府的愿望完全不符合现实。
在如此仓促情况下,南京保卫战的守军,号称总兵力11万人并不是生力军,除了小部分广东新来部队外,大部分是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而且这些军队刚刚溃退到南京,还没有喘息机会,敌军就已经尾随而至,根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出有效的守城布置。当然,唐生智作为守城司令官的失职也是无可推卸。历来坊间对于唐生智守南京流传许多风评,成为民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趣谈。
不幸的是,国民政府最高层官员的私人记录,也佐证了民间传说的正确性。

比如说,唐生智原本私下推测日军不会攻南京。因此当许多将领们认为南京守不了20天时,他却大唱反调说能守三个月。
徐永昌当即认为“此种判断似又出于军事政治以外。”徐永昌又听说唐生智相信密宗,颇多常人所不知者。所以只好无奈地感叹,“孟潇(唐生智字)真奇人也。”
事后徐永昌获得更多信息,得知唐生智耽于迷信,养一个术士在家,平日一切言听计从。他判断日军不会攻打南京,就是相信术士所预言,因此才敢坚决请求担任南京卫戍司令。连最后弃城的时辰也依照术士指示。因为他本来宣布在12月13日离开南京,但是术士说13是不吉利数字,因此他提前在12日离开,导致守军突然群龙无首,撤退秩序大乱,增加无谓死伤。
南京政府之所以信赖如此封建落伍的高官担任防守南京大任,一方面是它急于讨好地方实力派加入抗战阵营,任何人主动请缨它一定衷心欢迎。一方面又是对上海战争抱有过高期望,只看到成功而没有为失败预作准备,以致在上海大败之际,只能临时拼凑南京防务。1937年12月7日,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攻击。面对重炮和坦克的狂轰滥炸,中国守军不到5日便全面崩溃。依据何应钦报告,最后守城号称有12个师,共12万人,但是只有一半守军安全退出,伤亡和陷于城内约3-4万人,被俘可能万余人。

再依照白崇禧报告,守城军在出城渡江过程中,仅仅因为拥挤失控就造成七八千人死伤。
2、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的影响
用不着说,蒋介石也对南京战事感到痛心疾首。他在日记中写道,“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
到了1937年年底时,他回顾南京守城时又写道,“南京撤退各师长当时实情令人痛愤,此余用人不当有以致此,唐生智始终为误国之徒也。”
1938年初,蒋介石依然悔恨不已,再度宣泄纸上,“去年防守南京总司令不委唐生智,则敌或不敢攻京也。否则十一月杪敌国必不以陶德大使转达和平条件。及见我委唐守京,则敌即爽约猛进矣。以后应知,无将不如不作守城之计也。”
但是和其他丧地失职的地方实力派高级首领一般,唐生智也没有受到严重惩罚。在日军尚未兵临城下的空挡中,南京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故宫搬到南京的古物共一万五千箱抢救出城。
总体而言,所谓南京(首都)保卫战”实在无需被当做是一次单独战役来理解。
它只有一个模糊的、连政略都谈不上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不可轻言放弃首都。但是在事先没有经过慎密参谋作业,它也不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既没有建立战斗序列,也没有战术指导。有的只是一群精疲力竭的残兵败将,在撤退中仓皇被拼凑在一处,在一个无勇无谋而又贪生怕死的司令官统领之下,胡乱度过极度混乱的一周,随即成为悲惨的牺牲者,还殃及一大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老百姓丧生在日军屠刀之下。
陈诚在事后的评价是唐生智既不知国军力量,又误判敌人意向,加上“求出风头”,造成一次失败。纯从军事眼光而言,它只是淞沪战争的尾声。
然则国民政府所承受的军事和其他损失是什么?

经过淞沪战争和南京保卫战相继失败后,到1937年底,南京政府遭受了两个不同的损失。
一个最明显而且世人皆知的损失,是花费十年辛苦经营(1928-1937)所建立的所有重要的文化、商业、经济、工业和政治中心,在一夕之间付诸流水。
这120天(8月13日-12月13日)残酷激烈战斗都是在长江下游,中国过去几年现代化成果最精华的地带进行的,而国民政府也动用了几乎全部中央精英部队。根据王世杰接到的报告,国军投入淞沪一个战场的兵力相当于整个华北战场的兵力,可谓是国民政府全部的军事资源。
由于大多数中央军被布署在最重要据点,而采取的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步兵战术,因此在整场战役中中央军伤亡最为惨重,约有30万士兵战死在上海。
在南京保卫战中,国军伤亡速度更为惊人。在4-5天内,10-12万守军全盘瓦解。在华北,当许多地方实力派部队溃散窜离战场时,中央军也遭受了惨痛伤亡。至1937年底,中国部队共损失了37-45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作战总力量的1/3至1/2。
依张发奎估计,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精英大概丧失一半以上。阵亡者大约三分之一,受伤和重伤者三分之一。被俘和失踪人数很少。换言之,开战时动员的兵力幸存者不到三分之一。另据何应钦报告,国军从开战到1938年3月15日,官兵伤亡总数是49万余人(伤和亡大概各半);日军伤亡为18万余人。中日军队的伤亡比例是2.5:1。
开战前中国陆军号称共177个师,总共约2百万人(官佐136000人,士兵1893000人)。抗战爆发初期,中央军配备德国武器的有80000人左右,在淞沪战役中,中央精锐部队损失60%以上、低级军官伤亡10000人。战前10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这一次战役,损失10%,造成断层。

以上这些资料并没有精确性,一方面是战前的基本资料从来就不精确,一方面是战败军队根本无法统计损失。
3、长远的政治后果
另外一个则是当时并不显眼而后患无穷的损失,那就是它的长远政治后果。无可置疑地,长江下游战败的军事结果,是南京政府在德国顾问团,协助下建设出来的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殆尽。
而少数积极响应政府抗日救国号召的地方实力派部队(广东,广西)也承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相对而言,那些不肯参战,或是只做出参战姿态但又推三阻四不肯出兵的地方实力派,则成功地保全了实力,并且巩固它们的地盘。
就在这120天之内,在“舍身杀敌”和“口头抗日”的两股军事势力之间,其关系就因为“量”的变化而产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从全国军队组成比例而言,在华北和华东战场奋力抗敌的部队无不遍体鳞伤,亟需疗伤复原,而那些逃避作战的军队,却安然无恙地突然变成了中国军队的多数派。这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将会对此后整个抗日战争七年时期的党政军状态产生千丝万缕的后果。
依据一项估计,抗战开始时期,中国军队的组成大约是中央直辖部队共计编成35个调整师,24个整理师。它们在编制上大体成型,但是训练程度参差不齐。武器配备更不能和少数的精锐部队相比较。
而地方实力派军队荦荦大端者则有:东北军10个调整师;广东部队10个调整师;四川西康部队26-30个调整师,山西部队若干师。外加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的马家军和大量其他从来不曾在南京政府编制内,而遍布各省的各形各色地方部队,和没有部队番号的武力团体,无法细究。
到了1937年底,基本上中央直辖的调整师和整理师都已经瓦解或是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它们丧失了自己的根据地和生存依附,在此后七年战斗中成为四处漂浮的客居(寄居)部队,这个变化又进而逐渐腐蚀了它们的本质。
无可避免地,国军在淞沪战争惨败及南京防卫战的无能表现,也使日本信心大增。尽管蒋介石在12月16日再度发表了抗战到底的坚决声明,但是日本人认为可以很快结束战争,因此请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转递停战条件。
在陶德曼调停受到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后,日本就在1938年1月16日宣布,从此以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同时开始筹划对华进行长期用兵的准备。

但是由于日本主要担心的是苏联动向,因此不敢贸然向中国增兵,只求暂时在中国不扩大战面。相对有趣的发展是,蒋介石的态度反因为战败而愈加坚决。他在1937年11月中旬向政府高层领导人表示,尽管日本有德国意大利协助,但是世界上有英美法苏与之对立,只要中国抗战坚持下去,则日本必定陷于孤立。
不久之后,国民政府决定迁至西南大后方,目的就是使日本无法停止战争。徐永昌引用蒋介石的话说,“无论国际情形如何好,日本将来如何坏,还须我们自己不苟安腐化,能一心一德,则持久抗战,复兴民族之希望方能达到。”
显然地,蒋介石的心态已经从在长江下游和日本人决战,转移到以中国西南部为根据地和日本进行无止境的缠斗,而且强调必需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指望国际风云变幻,去和日本抗争到底。
南京政府在处理对日关系过程中,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早已把中日战争看成是不可避免,但是开战时机却需要小心把握。
大致而言,从1934年底开始,国民政府就着手拟定一个长程计划,要在全国编成60个师新军,预计完成目标期是1938年底。但是到七七事变时,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一半。即使完成德国顾问编练的60个师,全国还有三分之二的部队仍然是地方实力派部队。但是蒋介石希望这60个师可以大幅提升中国的总国防力量。
4、两难的选择
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面临两项艰难的选择是,在何处抵抗日本人和如何抵抗。
尽管这一消耗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为唤起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同时激起西方国家关注中日战争,但是当年的战略制订者并没有期待仅仅是靠一场战役就能够实现以上的预想。
相反地,蒋介石宣称这种作战方式,将会迫使日本身不由己地陷入在中国全部18省份逐一作战的泥淖之中。从这个意义去看,则淞沪战役并不是一场为迅速结束战争而挑起的突击战役,反而是一个处心积虑长期消耗战的开端。

最后,南京政府也曾经对中日双方可动员的军事资源进行过长期评估,而开辟淞沪战场的决策肯定受到了这些评估的影响。1937年7月,中国情报部门判断日本拥有现役兵员50万人,预备役240万人,海军120万吨船舰(列世界第三位),空军三千余架飞机。
相比之下,中国海军只是几十艘内河巡逻艇,完全缺乏能在海洋上作战的船舰,空军只有不足100架性能略好的战斗飞机。
中国陆军总兵力号称182个步兵师,依编制有200万名官兵,但是实际上可能不到170万人,而且有大批未经任何整理的部队,又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役,因此真正能用于第一线作战的部队低于半数。
虽然当时西方观察家,误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军事控制程度相当高,但是它实际掌握的仅有10万人的精锐部队与20万人的普通战力部队。我们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在兵员满额情况下,中国步兵师的火力配备约仅日本的三分之一。根据国民政府在淞沪战争中最高司令官的报告,即便是德国训练的中央军也不能够和日军相比。比如说,张治中属下的中央精锐部队每个师只有8000余人,而满额应该是12000人,武器更不能和日军相比。
而张发奎属下的部队是地方部队改编成为中央军,设备又不如中央军,轻武器是中国制造,炮兵更是缺乏。根据一项资料,全国部队的正规火炮大概只有457门,当然都是小口径。
更突出的差距是两国的装甲部队、炮兵,机动能力与后勤效率。日军一个师团配备有24辆战车、266辆机动车、555辆马曳车,而国军一个师却连一件也没有。根据徐永昌报告,连中国当时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每门炮都只配有3000发炮弹。在密集发射情况下,几个小时就会用磬。即使中方将此种有限的军事力量全部投入到单个大战场中,除非天运眷顾,否则国军很难占据任何优势。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正如一个资金匮乏的穷汉与财力雄厚的大款博弈。

前者基本上只有两种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要么是采取保守战略,每次投入小额赌注,期能“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扭转战略弱势。要么是采取高风险战略,在手中牌看似最好时押下全部赌注,期能“一战定江山”。
当我们将博弈转化为中日军事实力较量时,这两种战略也会产生全然不同的后果。
保守战略的优势在于能延缓敌军前进势头,争取时间以组建新部队,开发新资源或赢得外力援助。但是假如中国没有预备役部队可资利用,假如训练新部队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而成效尚且无法预卜,更假如国内没有潜在资源等待开发,而西方国家在短期内也看不出会施以援助的希望,那么这一战略对中方来说就缺乏吸引力。
相反地,采用积极进取的战略却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假如敌军原本就不打算扩大危机,那么中方坚决抵抗的姿态便能促使双方迅速达成停战。而假如敌军原本就执意扩大战事,那么积极的抵抗姿态至少也能消磨敌人的锐气,为中方赢得宝贵时间去着手把剩余资源西撤的计划。更何况敌国人民的情绪反应还是一个值得期盼的未知数。
因此,在南京政府看来,最初避免全面对抗,而后在内地实行运动战的战略隐含有巨大风险。
而如果在开战初期便坚决抵抗的战略则至少有两点明显优势。
第一,假如1937年日本人的意图与1932年同样保守的话,那么中国很快便能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包括华北),并且又能争取多几年时间去加强本身的军事建设。第二,假如日本人有更大更新的领土野心,那么中国至少也能保住些许筹码展开持久战。当然,这是风险巨大的赌博。淞沪会战所产生的悲剧后果并不在于战略构想的失误,而是战术执行的偏差。
国民政府若是有更多的精锐部队去防守上海南岸,阻击日军登陆增援,或是早几日下达撤退命令而井井有条地脱离战场,它就能以较小的军事代价换取巨大的政治胜利。既然蒋介石已经把手中的精锐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能够指望的就是更多的地方实力派能够向上海提供部队。

当这个设想落空而蒋介石必须把精锐部队当成是唯一赌注时,他只好依靠自己历来在战场上得到的经验,那就是,胜利成绩都应归功于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他所执着的信念,是“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
蒋介石这个个人信念很可能最能解释他为何在11月初依然要求将领们再坚持一段时间,而国际干预只是他能想出来的一个鼓励部属士气的好借口而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在上海没能克服妄念,总以为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导致日军丧失斗志,最终把原本大有希望的政治和战略胜利彻底演变为一场军事灾难。
回顾蒋介石在1933年初,曾经头脑清醒地对“雪耻”做出过长程性的规划。
他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整理基本区域,充实基本部队,筹备基本组织,选定基本人才,以树立革命中心,完成革命使命。”他又把这些工作称之为“今日谋国之道”的最重要项目。
但是由于他和主战派决定在淞沪地区全力反击日本,到了1937年底所产生的情况是:基本区域(土地人民)完全丧失,基本部队(中央军)彻底牺牲,基本组织(政府机构)大幅破坏,基本人才(公教人员)大量流失。换言之,十年辛苦几乎毁于一旦。在抗战的后继7年中,必须在一个陌生环境下营造一个新的基本地区,建立一支新的基本部队,修复基本组织,和网罗基本人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抗战才能进行下去。
蒋介石在战败前夕的10月底,曾经对此前10年的对日战策做过一个反思,他的分析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认为日本在亚洲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中国只是拦路石,因此日本务必加以移除才能免去后顾之忧。这就说明无论中国如何委曲求全和妄图妥协,均属徒然。中国唯一生路就是决心反抗,不可心存侥幸。依他冷静推算,即使中国承认满洲国也无法满足日本少壮派军人的野心。第二,他认为“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毙,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以求后人继起,复兴中华。第三,他认为即使是国际同情和干预也必须先由中国承受重大牺牲后才可能予以激发,而不是妄图挑起国际干预而躲避中国的牺牲。第四,抗战不论成败结果如何,都必须进行到底。如果指望不战而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换言之,不管有没有指望国际干预,中国都必须抗战。他的结论是,“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简配资-简配资官网-云南炒股配资-股票配资平台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线上炒股配资床垫内置AI智能健康睡眠系统
- 下一篇:没有了